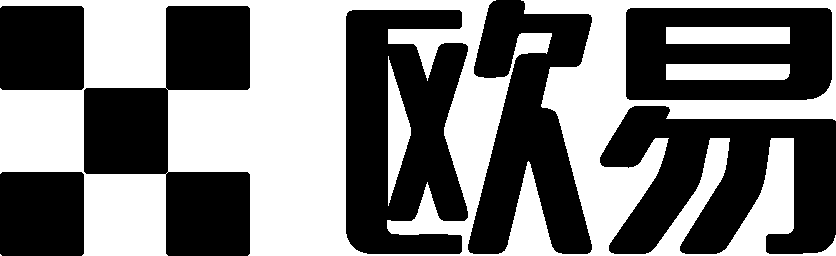当年张爱玲离开上海时,已经决绝地要与这里的一切断掉联系。
国内改革开放后,张爱玲姑姑张茂渊联系上了宋淇,给张爱玲寄去了第一封信。
姑姑此时,仍旧住在张爱玲走时的那个“卡尔登公寓”。
张爱玲回信叹道:“我真笨,也想找你们,却找不到,没想到你们还是在这个房子住。”
沧桑巨变之后的1981年。上海《文汇月刊》刊出张葆莘的文章《张爱玲传奇》。这是大陆报刊1949年以后第一次出现张爱玲的名字。
张爱玲在给弟弟张子静的信中说:“传说我发了财,又有一说是赤贫。其实我勉强够过,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,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。没能力帮你的忙,是真觉得惭愧,惟有祝安好。”
那一年,北大著名学者乐黛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,偶然看到张爱玲的作品,大为赞赏,于是辗转托人,想请张爱玲到北大做一次“私人访问”。
“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,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,所以不想回去看看。去过的地方太少,有机会也想到别处去……”
这里所说的“别处”,就是欧洲。张爱玲平生所憾“去过的地方太少”,就是指她一直未能去欧洲看看。
80年代中期以后,张爱玲“重归”中国现代文学史。大陆读者对张爱玲“迟来的爱”也汹涌而至。
张爱玲的代表作《倾城之恋》在《收获》杂志发表。掀起“张爱玲热”的第一波大潮。
1985年,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旧版《传奇》,这是内地最早出版的张爱玲作品。到1992年,安徽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《张爱玲文集》。“张爱玲热”走入了大众层面。
张爱玲搜集整理旧作,由台湾皇冠出版了《余韵》(1987)和《续集》(1988)两本集子。
而80年代中期,张爱玲为何要频频搬家?
据说,张爱玲有洁癖。她是在“躲跳蚤”,这个“跳蚤”,确乎是在她常住的房间里。为了“躲跳蚤”,据说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。
张爱玲“天天上午忙搬家,下午远道……去看医生。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,最后一段公车停驶,要叫汽车——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……”
一次,一位朋友去看张爱玲。“张女士!我是庄先生的朋友,我姓林!他托我拿东西给您!我跟您通过电话!”
屋里有了动静。“我衣服还没换好!请你把东西摆在门口就回去吧!谢谢!”
直到一年后,张爱玲为躲“跳蚤”开始频繁搬家,不得不求助于林式同,才打电话把林式同约来,在一家汽车旅馆的会客厅“接见”了他。
当时林式同看见,“……走来一位瘦瘦高高、潇潇洒洒的女士,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,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,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”。
——宽袍大袖是怕皮肤痒,走路无声息是穿了浴室用的毛拖鞋,头上包头巾是怕虱子而把头发都剪了。她晚年的装束一直如此,出门也穿毛拖鞋,有时戴上假发套。
张爱玲在频繁的搬家过程中,扔掉和丢失了不少东西,她自己说是“三搬当一烧”,不但把《海上花》的英译稿给弄丢了,连护照也不知何时被清洁工偷走,想去香港,也去不成了。
据夏志清讲,她不像夏志清他们看病有固定的私人医生,她看病,是到政府指定的专为穷人治病的免费医院,路途很远,要搭公车去,看病时还要等候多时。
洛杉矶的公共交通极不方便,去一个地方常要转车几次。稍有能力者,都要买部旧车代步;搭公车的,十有是穷人、流浪汉、不懂英文的非法劳工。可以想见,张爱玲装束怪诞,手提纸袋混迹其中,有如潦倒的bag lady“纸袋流浪女”!
从各方面资料来看,张爱玲这时收入已经不低,为何不找私人医生?
大家认为,张爱玲长期独居,过于封闭,且起居无规律、饮食简单,人也就老得快。
1988年秋,张爱玲写信告诉林式同,皮肤病好了,可以找固定住所了。还没等林找到合适的房子,她自己就在下城东边找到了一家公寓。张爱玲租住的公寓相当整洁。价格昂贵,每月380美元。走廊最里边的一个套间,家具齐全。门口有信箱和对讲机,信箱上用了她的本名E.ZHANG。 一天开12个小时的电视,大概是以此抵抗寂寞。偶尔出门,就是购物。她事先在随手拿来的小纸头上记下购物清单,比如咖啡、牛奶、胡桃派、熨斗、衣架、奶油、抹布、刮刷、香皂等等,然后出去,跑几家店一次买齐。偶尔也看报纸,不过都是挑着看,不大认真。去楼下取信的次数极少,十天半个月去拿一次,还要半夜三更才去,以防遇见人。在屋内,她只穿一次性拖鞋,觉得脏了就扔。不再打理发型,只以假发替代,也不再化妆,但是用很好的护肤品。
就在她自以为这样的“老鼠洞”生活绝对无人打扰的时候,她的隔壁,不声不响,住进了一位神秘女客!
这女客,是来自台湾的戴文采女士。很多张传都说她是“台湾某报”的记者。实际上,她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旅美作家。
戴文采其实并无恶意,虽然张爱玲对此类举动肯定要愤怒,但也多亏了戴文采的这次“卧底”,世人才得以了解张爱玲晚年的一个真实侧面:
她真瘦,顶重略过八十磅。生得长手长脚,骨架却极细窄,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,亮如洛佳水海岸的蓝裙子,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,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,像只收口的软手袋。因为太瘦,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始终撑不圆,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。午后的阳光邓肯式在雪洞般墙上裸舞,但她正巧站在暗处,看不出衬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,只觉得她皮肤很白,头发剪短了烫出大鬈发花,发花没有用流行的挑子挑松,一丝不苟的开出一朵一朵像黑颜色的绣球花。她侧身脸朝内弯着腰整理几只该扔的纸袋子,门外已放了七八只,有许多翻开又叠过的旧报纸和牛奶空盒。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,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,即使前倾着上半身,仍毫无下坠之势,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,我当下惭愧我身上所有的累赘太多。她的腿修长,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,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;我正想多看一眼,她微偏了偏身,我慌忙走开,怕惊动她。佯作晒太阳,把裙子撩起,两脚踏在游泳池浅水里。她也许察觉外头有人,一直没有出来,我只好回房,待我一带上门,立即听到她开门下锁急步前走,我当下绕另外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,她走着,像一卷细龙卷风,低着头,仿佛大难将至,仓皇赶路,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,在她背后私语般骇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,因为距离太远,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眼,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,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,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。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,甚至想起绿野仙踪。
这一篇采访记《我的邻居张爱玲》,洋洋万言。
她确是一个超级张迷,对张爱玲的语录信手拈来。关于“铜板”的那两句话,她说:“确实叫人十分抱歉,一口好井在人语喧哗中兀自凉着,也那样喜欢着外头世界的繁华,我们何必像顽童般非要扔石头惊她一惊呢?”
张爱玲马上搬家。她给司马新的信中提到“戴文采事件”。她说,她的地址,连她的姑姑都不知道,只是租用了一个信箱收信件。“中国人不尊重隐私权”,所以她不能住在港台。
1989年3月,张爱玲一直与外界隔绝着。张爱玲一次在过街时被一位中南美洲的青年撞倒,跌破了肩骨。她在给姑姑的信中说“这些偷渡客,都是乡下人,莽撞有蛮力”,看来是伤得不轻。
林式同是张爱玲晚年与之通电话最多的人。有一次,她说:“我很喜欢和你聊天。”
张爱玲在电话里抱怨牙痛,林式同就说:“牙齿不好就拔掉。我也牙痛,拔掉就没事了!”
张爱玲若有所悟,自言自语地说:“身外之物还是丢的不够彻底!”
1991年,张爱玲住的那座公寓,搬来了一些南美和亚洲移民,素质不高,嘈杂、不讲卫生。有人还养了猫,招来了蟑螂和蚂蚁。张爱玲不能忍受,给林式同写信说要搬家。
她提出了找房子的条件,有8项之多,其中有一条是,房子要足够新、没虫。 她信中说:“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”,“橱柜一格一罐”。 还有一条也很怪,是要求“附近要有火车”。她是喜欢听火车的声音。无论对生人还是熟人,她都恐惧;但是扰攘的“市声”,却是她的良友!
新居是单身公寓。在西木区(Westwood)。搬家的时候,她仍然坚持自己搬,不要林式同帮忙。这是张爱玲最后的居所,也是张爱玲在洛杉矶住过的最好的一个区,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很近。
伊朗房东打电话给林式同,说老太太经常忘记带钥匙,要他帮忙开门;又频繁抱怨浴室的设备有问题,要他去修理;还有诸如此类的麻烦事。
林式同早有思想准备,说:“她没有问题,过去还做过我的房客,按时交房租,不爱打扰别人,你尽管放心,有事找我好了!”
为了防止再有“卧底”跑来,她干脆在信箱上用了一个越南人的名字。房东问她是怎么回事,她说,自己的亲戚很多,都传说她发了大财,怕他们找上门来借钱。
1990年,台湾《中国时报》创刊40周年。报社邀请张爱玲赴台担任当年的“时报文学奖”评委,允诺评奖结束后,可出路费、派专人陪她去上海看望姑姑。她还是拒绝了。
1991年,张爱玲半个世纪的好友炎樱去世了。6月,姑姑张茂渊在上海逝世,享年90岁。
1992年2月,林式同收到张爱玲寄来的一份遗嘱副本。
遗嘱:“一、如我去世,我将所有的财产遗赠给宋淇和宋邝文美夫妇。二、我希望立即火化,不要存放在骨灰存放处,骨灰应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,如果撒在陆地上,应撒在荒野处。”
林式同后来说:“一看之下我心里觉得这人真怪,好好的给我遗书干什么……遗书中提到宋淇,我并不认识,信中也没有说明他们夫妇的联系处,仅说如果我不肯当执行人,可以让她另请他人。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子虚乌有,张爱玲不是好好的吗?我母亲比她大得多,一点事也没有……因此,我把这封信摆在一边,没有答复她。可是在张爱玲看来,我不回音,就等于是默许,后来我们从未再提起这件事,我几乎把它忘了。”见《有缘得识张爱玲》。
张爱玲对于生死问题,看得很开。可是,她没有留意自己最大、最具价值的一笔遗产——著作版权。
在她身后,皇冠出版社和大陆多家出版社为张爱玲著作的版权,打起了无穷无尽的官司。
张爱玲最后这几年是怎么过的,几乎谁也不清楚。她租住的公寓,位于西木大道与罗切斯特街交叉的地方,是一幢淡灰色的四层楼,门前有一棵松树和一棵棕榈树。公寓大门对面,有小书店、修鞋铺。
张爱玲给司马新的信里说:“剩下的时日已经有限……想做的事来不及做……” 她又有了小时候“穿上新鞋也赶不及”的焦虑。
进入90年代,她首先是编订《张爱玲全集》,准备收入已发表的全部著作。“皇冠”从1991年着手,一年以后就陆续出版。《全集》里的每篇文章都是张爱玲亲自校订,稿件在台北和洛城飞来飞去,耗费了双方不少的精力。
第二,是编一本图文并茂的《对照记》。
1993年11月的《皇冠》杂志上先行登出。而后在1994年6月,作为《张爱玲全集》第15卷出版。《对照记》一出,张迷们争相购买,又是一番洛阳纸贵的盛况。
该书收入老照片50余幅,从张爱玲的童年时起,到她40多岁止,50岁以后的一张也没有。其中有一幅,很值得一说。
那是1944年拍摄的一张,她原本穿着薄呢旗袍,但怕单色旗袍不上相,便又披了件浴衣在身上。
这幅照片后来“出镜率”很高——她颔首低回的样子,很有些惊艳。假如不是她自己说出来,谁能想到,照片上的服饰竟是临时凑合的!
中国人讲究凡事的结局要“大团圆”,一生要功成名就,子孙满堂。可是,张爱玲揣度自己的一生,莫说“成功”,就连一般人的“圆满”也没达到。她无头衔、无功名、无房产、无子嗣、无金婚之福,一辈子都是“无产者”。
《小团圆》的这一稿原定1993年内写完,在1994年2月“皇冠”40周年庆典时,与《对照记》合为一集出版。可是,后来因她身体不佳的原因,一再延期。此外,张爱玲还考虑,两书合为一集,书太厚,书价也会太高,于是要求先出《对照记》。
《小团圆》实际上有两稿,前一稿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动笔并完稿。据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表示,在整理张爱玲的书信时,发现她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,曾以英文撰写了23万字的自传性小说《易经》(Book of Change),因找不到出版社出版而作罢。
《小团圆》是张爱玲最为“神秘”的作品,创作历时约20年,几易其稿,却一直没有出版。文稿压在台湾皇冠文化公司创办人平鑫涛的手里,珍藏多年。
2009年2月23日,也就是台湾皇冠文化公司成立55周年纪念日的次日,《小团圆》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,由皇冠公司在台湾出版发行。
《小团圆》的面世,令广大张迷们极为兴奋,但也引起了一些人对出版方违背作者遗嘱的质疑。
张爱玲生前说:“这是一个热情故事,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,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。”
1995年9月8日,中国的“中秋节”前一天。
中午12:30,林式同回到家,正打算浏览当天的报纸,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,把他从沙发上惊了起来!
伊朗房东的女儿:“你是我知道的惟一认识Elieen Chang Reyher 的人,所以我打电话给你,我想她已经去世了。”
“我不信,不久前我才和她通过电话。”
房东女儿说:“我们几天没见过她,也没听见过她房间有任何声响,估计她已经不行了。刚才我已叫过急救车,他们马上到。”
据法医检验的结果,张爱玲大约死于六七天前,也就是9月1日或2日,死因是心血管疾病。
张爱玲平时不愿自己动手烹饪,也不愿到外面去吃,仅以罐头蔬菜、盒装鲜奶、鸡丁派、胡桃派、苏格兰松饼等作为饭食,罐头蔬菜用电炉加热一下就吃,充其量再煎个鸡蛋。如此长年累月,营养跟不上,免疫力下降,人都瘦干了。一遇大病,就顶不住了。
他亲眼目睹了张爱玲“家徒四壁”的极简生活之状。
墙上是空空的,没有悬挂任何装饰物。靠窗是一沓纸盒,这就是张爱玲的“写字台”,《对照记》、《小团圆》就是伏在这些纸盒上写的。
张爱玲还另外租了一个小仓库,有3英尺见方,里面收藏着她的英文著作、打字手稿等,都用手提袋装着。后来,在律师的帮助下,林式同遵照遗嘱的内容,把这些遗物分装十余个中型纸箱,寄给了在香港的宋淇。
在这些遗物中,有张爱玲的英文小说《少帅》、《上海闲游人》和未完成的《小团圆》、《描金凤》等手稿,除了《小团圆》外,其余至今尚未公诸于世。
9月19日,张爱玲的遗体在洛杉机火化。9月30日,是张爱玲75岁生日,按照中国的传统,是她的“七十六岁冥诞”。在这一天,她的骨灰,乘船护送至海上,撒向太平洋,同时还撒祭了红白玫瑰花瓣。
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在华人世界所引起的反响,可用“猛烈”二字来形容。
港台和大陆的媒体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消息,并刊登了有关的专访和悼念文章。受到华人媒体的感染,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和《洛杉矶时报》也有讣闻登出。
美国的华人文学圈中,人们自发地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。
国内的读者们,更是爆发出了空前的热情,有关张爱玲的书籍在海峡两岸再次热销。
可是,这一切对那已经完成人生谢幕的张爱玲来说,已经无涉了。人世的一切当成为过去式时,后人的追认,乃至放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“虚妄”则是别样的一种演出了。
实体的张爱玲,个人的张爱玲,一生在追求自由和希望的张爱玲,是永远“消失”了。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而精神的张爱玲,灵性的张爱玲,作品中的张爱玲,则依然在人们心中活着,乃至永生着。
zhufangmei
一路走来,一路看看。